阜陽颍上:驚堂一嗓大鼓響 余音綿延淮水長

演出現場。王林洪攝
“三根竹竿架上鼓,兩片板兒手中舞﹔張口道明甜與苦,唱遍颍淮今與古。”
這段朗朗上口的唱詞,是颍上大鼓書特點的真實寫照。
一聲聲大鼓震耳欲聾,一段段說唱勾人魂魄。從寒冬到酷暑,記者多次前往颍上城鄉,尋訪說書藝人,沉浸聽書意境,親身感受這項省級非遺的深厚魅力,像打開了一瓶陳年佳釀,回味綿長,心向往之……

演出現場。王林洪攝
颍上獨韻 兼容南北淮水長
立秋時節,颍上縣城。記者沿老護城河前行,在綠樹環繞中來到一處濱水小園,一幢古色古香的小閣樓映入眼帘,樓裡不時傳出渾厚有力的大鼓金腔。這裡,就是颍上縣文化館曲藝社——聽大鼓書的地方。
“想聽懂颍上大鼓書,得先了解它的來源和特色。”走進樓內,記者見到颍上縣文化館曲藝社名譽主席萬文孝。75歲的萬文孝是文化館老館長,退休后仍為颍上大鼓書操勞著。
他告訴記者,大鼓書最早興起於宋明兩代,從北京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傳播開來。傳入颍上后,逐漸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颍上大鼓書。
“颍上大鼓書是一種說唱兼具的曲藝藝術,本地俗稱‘打鼓說書’,曲調多源於颍上傳統民間音樂和地方小調,唱詞多為七言或十言的上下句體,用颍上方言敘事抒情,既有北方的豪邁之氣,又有南方的細膩之情,別具一番風味。”萬文孝介紹,與河北遷西、安徽全椒等地流行的“雙人大鼓”不同,颍上大鼓書是一人表演,一張嘴、兩片板、三釵竹架支上鼓,就是全部家當了。
萬文孝告訴記者,上世紀五六十年代,颍上大鼓書進入繁盛期,大鼓書藝人走南闖北,走街串巷,以唱書討生活,逐漸流行於颍上、阜陽、阜南、霍邱等地,常出現全村人齊聚聽書的盛況。最早,唱詞內容多為歷史演義、武俠公案、戰爭場面等,即為‘舊書’﹔60年代以來,創作了不少以鄉村生活、政策改革、語言典故為主的唱詞,被稱為‘新書’﹔80年代后,隨著電影電視等娛樂形式豐富普及,颍上大鼓書進入低潮期,鼓聲逐漸稀落,聽眾越來越少。
“好在,2013年,颍上大鼓書被列入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。”萬文孝說,目前,颍上縣能唱大鼓書的不過百人,常來曲藝社演出的隻有四五個人。省級非遺傳承人有路佔軍、姚新文,市級非遺傳承人有王祥學。“正好,王祥學正在演出廳唱著呢,咱們過去聽聽。”
說唱相融 妙趣橫生人入迷
步入演出廳,隻見門前挂著“今日演出海報”,上書:大鼓《大唐平妖傳》第一場《羅元下山》。
戲台上,大鼓書藝人王祥學身著紅衣白褲,面前架著一面紅色小鼓,右手拿鼓槌,左手持木板。
戲台兩側,一對紅燈籠旁挂著一副對聯:“展非遺風採演曲藝藝術,娛千家萬戶樂百姓生活”。
台下,二十多位老人端著茶杯,半倚在藤椅上,瞇著眼睛,隨著節奏搖頭晃腦。
“哇呀呀呀!”隨著一陣細碎鼓聲猛地打住,王祥學突然喊道:“各位書友,穩坐兩旁,聽俺掃不帶板,這可就來啦……”王祥學拖著長腔,舞動著手中的鼓槌和木板,說唱起來:“您往大道看,雙陽道咯楞楞才把戰馬鬆,跑來兩匹馬上坐兩位大英雄。猛抬頭,前邊來到八水長安那座皇城,兩員將鞭敲戰馬往前行,恨不得肋生雙翅能騰空。”
觀眾正好奇,王祥學說詞驟停,轉而獻上一段急切鼓聲,“吊足”了觀眾“胃口”。
“颍上大鼓書,唱法上有‘臥嗓’‘立嗓’之分。”萬文孝輕聲介紹,剛才這段音色剛勁的唱腔是臥嗓,聲音沉穩,吐字清晰,一般用於普通的敘事或抒情。立嗓,往往要配合唱詞中人物情緒或故事情節激昂的片段,更能喚醒聽眾的耳朵,讓人振奮不已。“你聽,接下來該是立嗓了。”
說話間,王祥學“嚯”地一聲突然站起身來,將雲板舉過頭頂,叮呤咣啷地敲響起來。“今天,這兩員將要把長安進,能鬧得,山崩地裂海水紅。”他提高音量,改說為唱,音質渾厚嘹亮,配合“三輕一重”鼓點,一字三轉,把節奏拖慢了下來:“您要問這是咋回事?倆人又叫什麼名?書友們別發躁,您等俺把來歷都說明。”
“大鼓書藝人總能在觀眾最感興趣的時候或戛然而止,或拋出引子。這叫‘扣帽’,就是制造懸念,扣人心弦。”萬文孝解釋,一場書要大扣套小扣,小扣連大扣,一個扣子還未解開,另一扣又套上。“這樣一來,我們都被扣在情節中啦。”
因方言問題,有些唱詞記者沒聽清楚,但王祥學一言一行中都洋溢著激情,像個威風凜凜的大將軍,吸引記者往下猜,對接下來的故事情節充滿了好奇。
他接著唱,忽而抑揚頓挫,轉而婉轉悠長,繼而如泣如訴、嗚嗚咽咽,時而激昂大義、慷慨陳詞,並輔之以動作,繪聲繪色地演繹著。“就看這個大蛤蟆,蹦跶,啊蹦跶,就蹦進屋裡頭嘍……”又是一聲驚堂鼓響起,說到關鍵處,王祥學賣起了關子:“要問后來怎麼樣,且等著下回您再聽……”
一曲唱罷,記者不禁和大家一起拍手叫好,直呼沒聽夠。
苦練絕技 為“藝”消得人憔悴
“我是颍上縣夏橋鎮人,今年62歲,16歲就跟著師傅江志軍學大鼓書了。”王祥學走下戲台,記者趕忙上前採訪。他身材高大,昂首挺胸,皮膚黝黑,長著一對招風耳。
王祥學在家排行老小,上初三時,師傅來村裡唱書,聽了一次就上癮了,想知道后面的故事,翻牆頭逃課也要聽,晚上回家還想著書。后來,學也上不下去,干脆不念了,他和家人吵了一架,跟著師傅走了。
“學大鼓書難吶。”王祥學說,天南海北到處跑,吃住還不如家裡,師傅脾氣不好,挨打罰跪是常事。“一次,我被打得跑回了家,躺了兩天還是想學書,又回去找師傅,決心一定要學成。”
師傅教王祥學的第一出戲是《花英打擂台》。那時沒有錄音機,王祥學隻能靠耳朵聽,把5000多字的唱詞抄在紙上,翻來覆去地背,熬得整夜不睡覺。“第二天雞一打鳴,我就開始嘰裡呱啦地念,念到滾瓜爛熟,把嘴皮子練利索。”說著,王祥學展示了一個選段,記者盯著看,他的嘴唇像打機關槍一樣,一分鐘竟能吐出300多個字。
記者發現,王祥學的嗓子比一般人都要“亮”,聲音也更粗獷,平時說話也像唱大鼓書一般,抑揚頓挫,中氣十足。“這都是從小練的,嗓子是大鼓書藝人的命,愛惜得很。那時候,我到哪兒唱,書友都能聽出來我的嗓音,還給我起了個外號‘颍上垮小王’。”王祥學邊說邊拿出隨身帶的黃氏響聲丸和一個磨出包漿的水杯,喝了一口。打開水杯一瞧,裡面泡著甘草、麥冬和胖大海。憑借一口金嗓子,王祥學逐漸在當地大鼓書“江湖”上站穩了腳跟。
除了嘴皮快、唱腔亮外,王祥學還有一個秘訣——唱詞妙。“師傅先教給我‘書帽’,就是開演前吸引觀眾的那一段詞,再教我‘片子詞’,即描寫人物樣貌穿戴、樓台殿閣、環境氛圍的片段唱詞,還讓我背詩詞歌賦。這些都熟練后,我開始學唱成章節的‘大部書’。”王祥學說,“學大鼓書就像蓋房子一樣,書裡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故事梗概是固定的,相當於地基,具體的情節和用詞就像屋裡裝修,靠藝人用‘十三條大韻’潤色編寫,將其變成通俗易懂且平仄押韻的唱詞。”
“唱詞生動還是干巴,決定了能否留得住聽眾。大鼓書考驗藝人的表達能力,要說得活靈活現,唱出酸甜苦辣,吸引男女老少,讓他們聽得有‘味’,像吃菜一樣。”王祥學說,前提就是說書人自己要讀足夠多的書,將故事內化於心。“我看過的書,少說也有千兒八百本了。一本一本地看,一章一章地改,有時候,為了一個韻腳反復要修改十幾遍。”
在王祥學拿手的大鼓書唱詞中,最令他滿意的有《包公奇案》《劉秀走南陽》《美人贊》《小八義》等。
“好一個劉秀漂泊龍,被追殺場中,龍目掉下淚,蒼天連連嘆幾聲。想我劉秀虛度年華,十三年歲如一夢,天意已定難改更……恨蒼天,您不睜眼,怨大地,怎無情,今生難把冤仇報,大漢江山化為風。”
王祥學的腦子像是一台計算機,可以任意調出一段唱詞,也能隨時隨地現編一段。
“張口就來了啊!老王我抬頭觀,打量對面站個女嬋娟。看大不過20歲,看小不過少一年。不高也不矮,不胖又不瘦,鼻梁骨兒高,襯著櫻桃口,美天仙還要比她丑,嫦娥見她也害羞。”王祥學突然給記者來了一段“私人訂制”,一邊說唱,一邊扮著滑稽的動作,逗得記者笑個不停。
“學藝難吶!我們這些人,都是受了脫幾層皮的苦才學成的,這才一直不願丟。”王祥學說。
崇德向善 唱詞教化潤心田
朱心一,今年66歲,家住十八裡鋪鎮。他19歲學藝時,正趕上颍上大鼓書藝人最受歡迎的時候,幾乎所有集鎮都有大鼓藝人設場表演。
“我小時候,隻有最窮的人家才舍得把孩子送去學大鼓書。后來,喜歡聽書的人越來越多,說書藝人掙錢多了、地位也高了,大家都說‘手藝不如口藝’哩。”朱心一說。
颍上縣曲藝協會秘書長吳多超告訴記者,說書行當吃香,是因為那個時候農村交通閉塞、信息封閉、休閑娛樂方式單一。“颍上大鼓書接地氣,成了農民的精神大餐,潛移默化走進了老百姓的生活中,增添了不少樂趣。”
“農忙剛過,大鼓書藝人就來了。沒啥事兒干,我和兄弟幾個就跑去聽書了。”說起當年聽大鼓書的情景,今年80歲的江口鎮村民張世昌說,那時候管聽書叫“集膽”,交5分錢,算是買了票,蹲在一旁聽,感覺很過癮,大家笑著、樂著,整個村子都是暖烘烘的。“從盤古開天地,聽到唐宋元明清,現在還記得不少故事,偶爾還講給小輩兒聽。現在,老一輩人或多或少都能說幾句大鼓書唱詞。”
“很多村民沒有讀過四書五經,甚至大字不識,書中的道理看不懂,聽書卻聽得明白。”朱心一邊說邊唱:“‘大鼓一敲咚咚響,父老鄉親聽俺講。一臣不保二君主,忠臣不保二君房。’這是《楊家將》選段。‘乾坤不動日月忙,萬物生長靠太陽。都希望孩子發展好,教育子女靠家長。家長就是好老師,好老師才能教出好棟梁。’這是《做一個合格的好家長》選段。”
據朱心一介紹,大鼓書裡,有奸臣當道、忠臣受害,有公子落難、姑娘含冤,故事的結局都是好人有福報,壞人作惡沒有好下場。《打天破寨》,唱正直勇敢的英雄好漢,教人懲惡揚善﹔《勸事文》,唱“三綱五常”,勸夫妻、勸兄弟、勸學生、勸鄉鄰,叫世人為人為家為國有擔當。“颍上大鼓書無形中框正了人們的為人之道、處世之理,對當地百姓的人格修養塑造,道德觀、歷史觀的形成發揮了教化作用。”
“唱得動人心算為妙,唱不動人心枉大功。路邊看見鄰居正吵架,唱上一段,唱得兩家拉著手笑哈哈﹔誰家婆媳鬧別扭了,唱上一段,唱得媳婦像婆婆親生的娃。講古書,品俗理,大鼓書總是勸解人心、教人向善的良言。”朱心一驕傲地說:“從前,我們大鼓書藝人被尊稱為‘先生’,鄉鄰們請我到家裡去,是要進堂屋坐上座的,吹響、雜耍的藝人可沒有這待遇。”
53歲的李家寶打小在阜城河東片區長大,他七八歲時常見到颍上來的“先生”在集上唱大鼓書。對“先生”說的話深信不疑,聽著聽著仿佛身臨其境,如痴如醉,甚至連續幾個晝夜都在回想,樂此不疲。
“想象著穆桂英、樊梨花的英姿,關公紅臉眉須的威武神態,感動於霍去病、岳飛報效國家的高尚品德,同情林沖、武鬆的淒涼境遇。此時此刻,歷史好像都在大鼓書中復活了。”李家寶告訴記者,自己最喜歡聽的還是楊家將、綠林好漢的故事,受書中好漢忠孝節義的影響,長大后,他成了一名保家衛國的軍人。
酸甜苦辣 一生痴情難舍棄
記者採訪時,一位長者在一旁默不作聲地看著聽著,偶爾上前添茶倒水,表演散場后佝僂著身子掃地。起初,記者以為他是一位保潔,打聽才知,他竟是名噪一時的颍上大鼓書藝人陳家勇。
“他身上的故事多哩很,這輩子和颍上大鼓書分不開嘍。”王祥學指著陳家勇說。
陳家勇個頭不高,身材瘦削,戴著一副眼鏡,背心和襯衫洗得發白,滿臉皺紋卻始終笑盈盈的。
“我是盛堂鄉人,屬猴的,比王祥學大不了幾歲。你看,我比他顯老得多。命苦哇,操心操的。”陳家勇說,“我從小就愛玩愛演愛學,家裡窮,隻供我上到四年級,13歲就進了師傅張永雲家,跟著他沿淮河兩岸走,說書討生活。”
17歲,陳家勇出師單干時,還帶著娃娃腔,走到村裡、街上說書,大家給2分、1毛的,豐儉由人,有的還給他拿糧拿饃。就這麼走著唱著,到了20多歲,陳家勇嗓子慢慢“亮”了起來,唱詞也更加熟練,隨便走到哪個村子都能圍上100多人聽,有的生產隊一給就是兩三塊錢。“那時候錢值錢,1毛錢一個白饃,3毛錢一碗雜燴湯。城裡干部一個月才拿60多塊錢,我一個月能掙得100多塊,不僅養活了自己,還能顧得上家。”
就這樣,陳家勇攢了錢,娶了媳婦,生了3個男孩。“鄰裡鄉親都說我家過得好,可誰能知道后來呢。”陳家勇頓了頓說,“我媳婦31歲時意外去世,我一個人拉扯三個兒子生活,沒法出門唱書,孩子跟著我沒少受罪,村裡頭沒有人不可憐俺們的。”
“等孩子們大了些,我能出門唱書了,聽書的人卻越來越少﹔再后來,有了聽戲機、電視、手機,根本沒人願意聽書了。”陳家勇說,“我的師兄弟也都背著大鼓回家了,有的經商,有的種地、做零活,以前掙錢吃飯的活計,隻能在茶余飯后拿出來唱著玩了。”
“我跟兒子們說,上有天下有地,無論遇到啥再難的事,都不能起壞心,不能做壞事,咱們得憑良心做事。”說話間,陳家勇隨口唱了兩句:“挺起來腰別泄勁,別笑話窮人穿破衣,三十年河東轉河西。”
“再說大鼓書吧。”陳家勇回憶,2010年前后,不少老藝人給颍上縣文化館寫信,希望能保護好颍上大鼓書。縣裡逐漸重視起來,舉辦鼓王爭霸賽,籌建曲藝社演出廳,老藝人又聚在了一起,輪流到曲藝社演出。
“群眾來演出廳聽書全免費,藝人說書由文化館補貼,演一場130元。我又能靠大鼓書掙錢了,書友們說我唱得好,我更起勁了,從家裡騎自行車,來回20多公裡,就數我和王祥學來得最多。”陳家勇說,
2016年前后,陳家勇被查出慢性支氣管炎,住院治療后,他還想唱書,書友們卻不讓他唱了。“我知道,唱書得靠一口丹田氣。我和大家說,讓我唱兩句,要是唱不下去,我就下台。高高興興是過一天,愁眉不展也是過一天,隻要我一唱書,那些傷心事就都忘了。”
2022年患上新冠后,陳家勇身體大不如前,但還想來曲藝社唱書。社領導讓他回家修養,他急了,寫了個“軍令狀”:我來唱書,病了、死了跟曲藝社沒關系。陳家勇說:“領導看我這樣,心也軟了,說曲藝社缺個打掃衛生的,一個月1800塊錢,問我可願干。我願意,從那之后每天都來。對別人來說,大鼓書不唱了還能去打工、務農,但對我來說,大鼓書就是全部了。”
如今,陳家勇7點准時到曲藝社開門,掃掃地、擺擺桌椅,找人寫“今日演出海報”。中午,他在曲藝社附近的老年助餐食堂吃飯,下午1點半便提前打開空調,噴上驅蚊水,燒一壺水,灌進保溫茶瓶,再燒一壺水晾涼,等著藝人和書友們前來。“我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,今年過年還攢了1萬塊錢給考上大學的孫女當獎學金。”日復一日的重復,陳家勇樂在其中:“雖然現在唱不動了,但我願意在曲藝社裡待著,離大鼓書更近一點。”(李一晴、段曉旭)
來源:阜陽日報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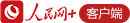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